目录
快速导航-
卷首语 | 大语言模型的“语言”跟自然语言性质迥然不同
卷首语 | 大语言模型的“语言”跟自然语言性质迥然不同
-
“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二十年”多人谈 | 网文是语言生活研究的一个新课题
“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二十年”多人谈 | 网文是语言生活研究的一个新课题
-
“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二十年”多人谈 | 语言生活问题的捕捉、发掘与提炼
“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二十年”多人谈 | 语言生活问题的捕捉、发掘与提炼
-
“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二十年”多人谈 | 中国“语言生活派”的返本开新
“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二十年”多人谈 | 中国“语言生活派”的返本开新
-
“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二十年”多人谈 | 规范与认同:从语言定义审视LPP 的学科属性
“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二十年”多人谈 | 规范与认同:从语言定义审视LPP 的学科属性
-
“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二十年”多人谈 | 语言规划须因时而变和因地制宜
“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二十年”多人谈 | 语言规划须因时而变和因地制宜
-
“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二十年”多人谈 | 语言生活是一个包含语言规划的整体性概念
“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二十年”多人谈 | 语言生活是一个包含语言规划的整体性概念
-
“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二十年”多人谈 | 语言生活民族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
“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二十年”多人谈 | 语言生活民族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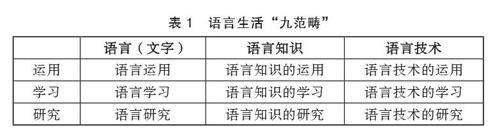
特稿 | 二十年来的中国语言生活研究
特稿 | 二十年来的中国语言生活研究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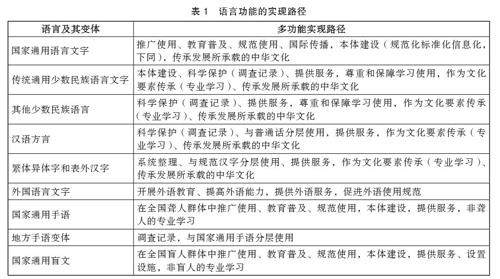
专题研究一 语言立法 | 语言功能规划视角下的新时代语言立法
专题研究一 语言立法 | 语言功能规划视角下的新时代语言立法
-
专题研究一 语言立法 | 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研究的回顾与思考
专题研究一 语言立法 | 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研究的回顾与思考
-
专题研究一 语言立法 | 国家认同视域下的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修改
专题研究一 语言立法 | 国家认同视域下的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修改
-
专题研究一 语言立法 | 当代俄罗斯的语言立法与语言关系发展
专题研究一 语言立法 | 当代俄罗斯的语言立法与语言关系发展
-
专题研究二 大语言模型 | 描写还是解释:由ChatGPT反思语言学的两种目标
专题研究二 大语言模型 | 描写还是解释:由ChatGPT反思语言学的两种目标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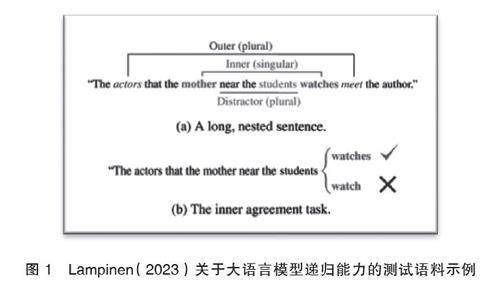
专题研究二 大语言模型 | 国际学界关于ChatGPT语言能力的争论与思考
专题研究二 大语言模型 | 国际学界关于ChatGPT语言能力的争论与思考
-
专题研究二 大语言模型 | 大语言模型在哪里挑战了语言学?
专题研究二 大语言模型 | 大语言模型在哪里挑战了语言学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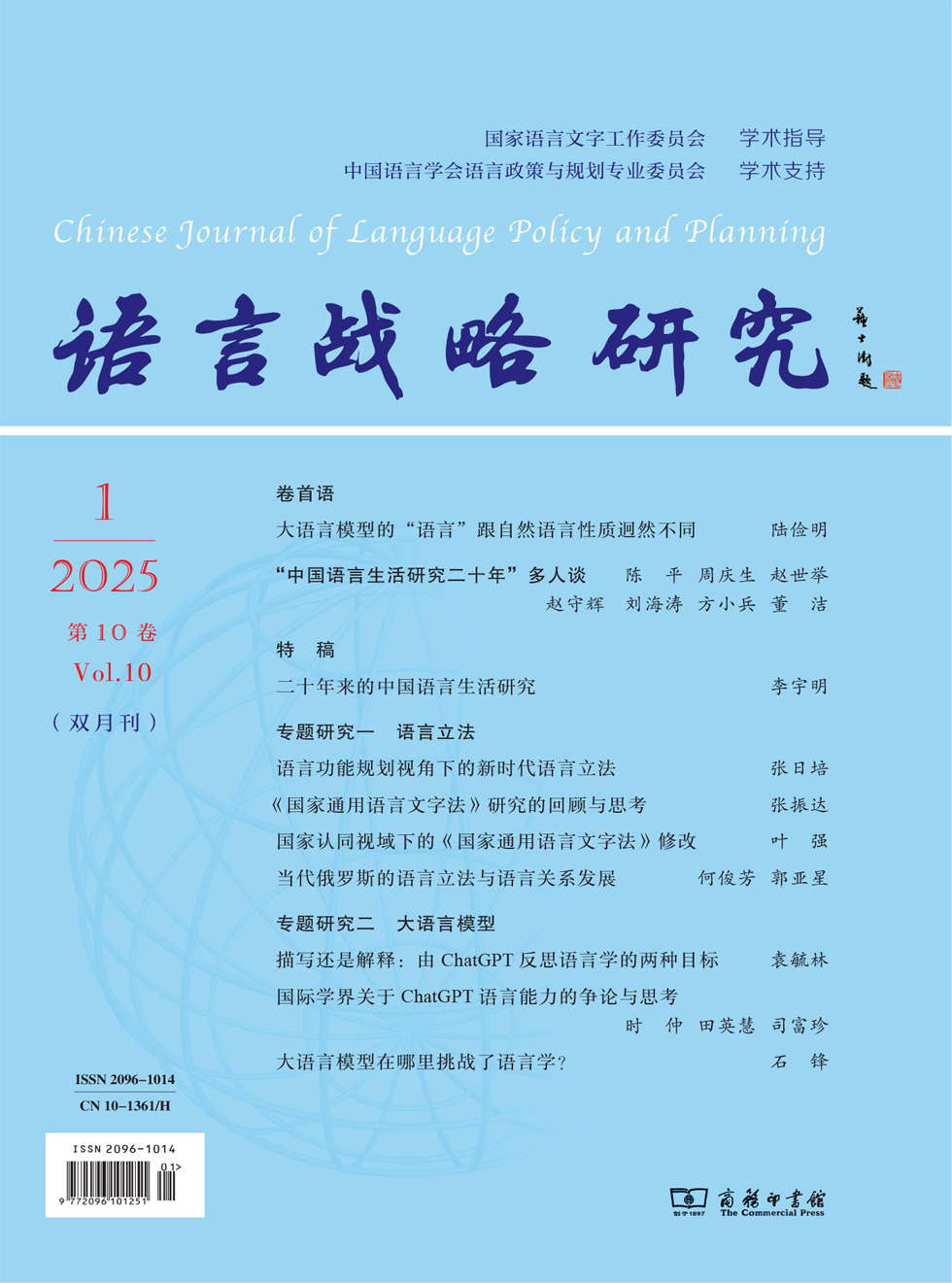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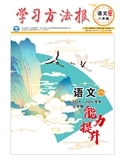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