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全部分类/
- 文学文摘/
- 当代人
 扫码免费借阅
扫码免费借阅
目录
快速导航-
开卷 | 向新而生 向新而行
开卷 | 向新而生 向新而行
-
小说坊 | 焰火
小说坊 | 焰火
-
小说坊 | 月牙泉边
小说坊 | 月牙泉边
-
小说坊 | 我爱江小山
小说坊 | 我爱江小山
-
小说坊 | 淡饮茶
小说坊 | 淡饮茶
-
小说坊 | 吴芝儿湖
小说坊 | 吴芝儿湖
-
小说坊 | 三爷
小说坊 | 三爷
-
小说坊 | 二十粒松子
小说坊 | 二十粒松子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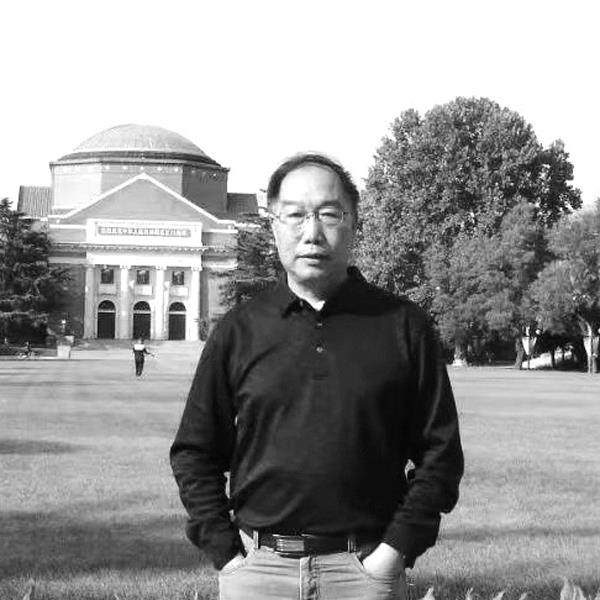
对话录 | 河北现当代文学传统的生成逻辑与时代品格
对话录 | 河北现当代文学传统的生成逻辑与时代品格
-
新文采 | 暖村牙事
新文采 | 暖村牙事
-
新文采 | 出海
新文采 | 出海
-
新文采 | 鲜汤
新文采 | 鲜汤
-
新文采 | 三畤原手记
新文采 | 三畤原手记
-
新文采 | 写给Y的N封信
新文采 | 写给Y的N封信
-
新文采 | 兄弟你好
新文采 | 兄弟你好
-
新文采 | 蓬勃土炕
新文采 | 蓬勃土炕
-
诗歌潮 | 温泉村
诗歌潮 | 温泉村
-
诗歌潮 | 张北叙事
诗歌潮 | 张北叙事
-
诗歌潮 | 奇迹及其他
诗歌潮 | 奇迹及其他
-
诗歌潮 | 一旦它钻出我的皮肤
诗歌潮 | 一旦它钻出我的皮肤
-
诗歌潮 | 说起一生
诗歌潮 | 说起一生
-
诗歌潮 | 忽忆故园
诗歌潮 | 忽忆故园
-
诗歌潮 | 落叶
诗歌潮 | 落叶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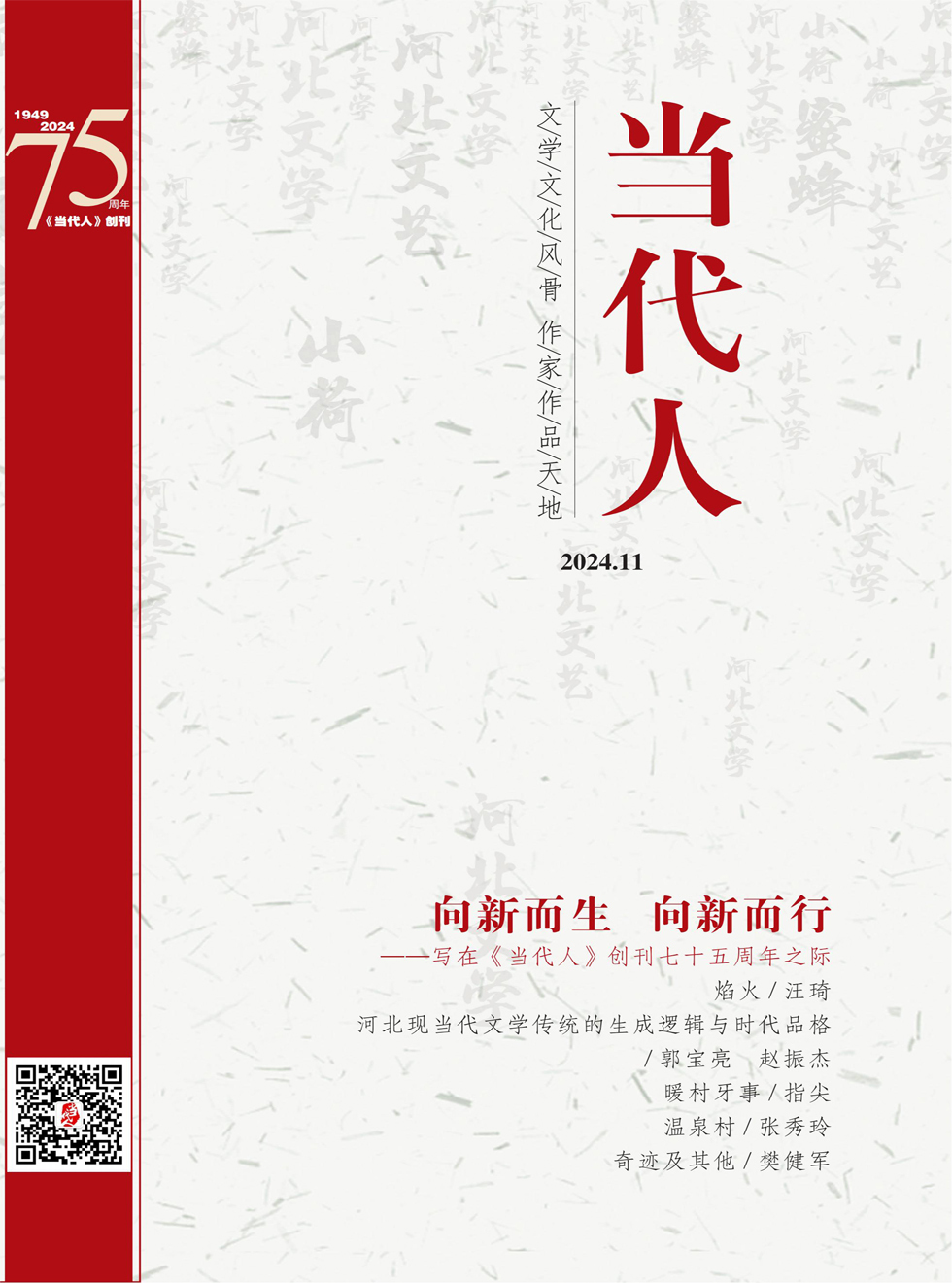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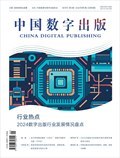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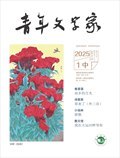

 登录
登录